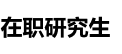“中國宗教研究方法的新視野”工作坊在復旦大學舉辦
近幾十年來,隨著宗教研究各項議題的全面展開,學術界對中國宗教學的理論建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國宗教研究范式的構建工作也日顯迫切。在此學科建設的內在要求之下,如何做到既能用整體的眼光看待包括儒、道、佛以及民間信仰在內的中國宗教傳統,又找到適合各自研究對象的具體方法,并且能認真地回答社會各界提出的信仰和宗教問題,是擺在中國宗教學者面前的重大問題。為此,復旦大學哲學學院與北京大學哲學系宗教學系聯合發起系列研討,共同反思和推進中國宗教研究的方法論。繼今年六月在北京大學之后,2018年12月1日在復旦大學舉辦了“中國宗教研究方法的新視野”工作坊。
工作坊由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宗教系李天綱教授、北京大學哲學系宗教學系張志剛教授共同主持。作為工作坊的一部分,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蒲慕州,于11月30日做了題為《漢唐之巫蠱、政治與宗教心態》的講座。講座分為巫蠱之源起、漢唐宮廷巫蠱事件概述、施蠱者之身份分析、被害人之身份分析、巫蠱事件反映至社會及宗教心態與現實。蒲慕州最后指出,我們對巫蠱的理解,不止于認識到它是一種民間信仰,或者是一種被人們有意識地利用來達到迫害他人的借口,更要考慮它之所以會成為有效的借口的生理、心理和社會原因。
在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宗教學系郁喆雋教授主持的“中國宗教”多人談的學術沙龍上,張志剛提出中國宗教學研究的兩個關鍵詞:比較和對話。從比較到對話,比較是宗教學學術研究的起點。對話是圍繞全球化時代、人類關注的重大問題。他以宗教觀為切入點反省,回到中西方碰撞的開端,討論信仰與理性的矛盾沖突。
北京大學哲學系宗教學系李四龍教授談了佛教研究方法的新趨勢,他提出要用世界史的眼光和解經學相結合的角度,進行方法和領域的開拓。他認為,過去佛教研究強調了佛教與中國文化的關系,現在要多考慮中國宗教如何融入世界文明中,將中國佛教史看做是世界文明史的組成部分。
北京大學哲學系宗教學系的程樂松教授以李天綱的新著《金澤》為例,指出生活世界作為基底的敘述和分析視角,讓信仰研究擺脫了“日常-神圣”的二元框架。信仰顯然不是為了在生活世界之外辟出一個飛地,面向超越地展開與日常性對偶的另一個語境,恰恰相反,信仰很大程度上以周期性的行動的方式達成對日常生活秩序的心靈認同,并指向日常生活中的諸多需求。信仰的內在性不依賴教義或教條的貫徹,而是保持著與生活協同的高度彈性,這種協同感是生活世界的腠理和機制保障。
在第二天舉辦的工作坊中,北京大學哲學系宗教學系的王群韜博士以清代山西澤州府地區的三教合祀的“三教廟”為例,依據方志、碑刻、田野考察資料,圍繞三教廟的“城-鄉”分布格局、信仰人群構成及其與地方文化傳統之聯系等問題展開考察,力圖探究這一“普遍存在的特殊信仰形式”所蘊含的中國民間信仰傳統與習俗,并嘗試提供一種民間信仰研究的新視角。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范麗珠教授發言題為《宗教社會學中國宗教研究的理論建構 ——從“神道設教”談起》,她認為,楊慶堃在《中國社會中的宗教》提出的“彌漫性”宗教概念,說明了“宗教”確實存在于的中國親屬體系、家庭和經濟團體,社區,國家以及儒教作為制度化的正統學說之中,而“神道設教”就是與制度性(組織性)的中國宗教的根本性特征。對“神道設教”的宗教社會學功能主義的分析,可以認識中國社會的“帶有終極道德意義的體系”的儒教特征,并與民間信仰和釋道兩教的實踐有機地串聯起來。復旦大學宗教與國家安全智庫陳納研究員也從儒教與孔教的定義問題出發,討論了作為中國宗教的名稱、定義、范圍及社會作用。
最近幾年,中國宗教研究領域出現了不少采用社會科學(包括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研究方法的成功之作,突破了一般的義理式的宗教研究,也帶來了新的挑戰。華東師范大學社會學系李向平教授的發言,切實地描述了這一現象,并給工作坊提出了這一問題。北京大學哲學系宗教學系沙宗平副教授以《人文立教與神道設教之交涉》為題,進一步討論了人文宗教與神道設教之間的關系,指出神道教與人文教并不矛盾,且相互補充。兩者在研究方法上可以不同,既需要義理闡釋,又需要田野調查。李四龍教授則提出當前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興起以后,仍然需要保持“人文宗教”的傳統研究方法,即按文獻、經典、教義、教儀等文史哲學科方法來研究中國宗教,以深入闡釋人類信仰深刻的精神傳統。中山大學哲學系李蘭芬教授的發言,不約而同地呼應了這個觀點。她以《湯用彤的“為學”能“成”什么?》為題,討論了湯用彤先生在哈佛大學開創的用西方現代社會科學方法,結合哈佛式的人文主義哲學關懷來研究中古佛教的方法,頗能引申到儒家宗教性問題的討論中啟發后來的學者。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學愚研究員以《當代中國佛教研究的觀察與反思》為題發言,傳達出的信息表明當前的人間佛教研究,已經突破了單純義理的辨析,進入到翻譯和比較,文獻和檔案的實證階段,除了對“彌散性”的民間信仰,三教混同的中國宗教有集中的討論之外,參加工作坊的各地學者還對中國宗教的組織方式進行了新的剖析。中國宗教,雖不似西方宗教那樣的“教會”(church)組織方式,但也在數千年的信仰實踐中形成了強弱不一的組織方式。復旦大學古籍保護研究院研究員王啟元就他熟悉的明清佛教的構成方式做了具體說明;復旦大學中文系講師陳特就中國宗教的Institution問題按其本意做了細致辨析,均表明中國宗教傳統自成一體。佛教、道教自是有宗有派,就是儒教、民間宗教也有著獨特的組織方式。近代以來,學界大多以“民間宗教”和“民間信仰”區分有組織的會、道、門和無組織(其實是弱組織)的香火祭祀。過去把兩者劃分得很清楚。
2011年以來,北大、復旦,還有港中大、臺政大的學者在華人宗教研究系列四校論壇,以及復旦、北大的系列工作坊中提出:民間宗教和民間信仰兩者之間的區別并沒有那么截然。事實上,香火祭祀,日常拜拜中也有相當重要的社群聯系方式,如“會”,如“社”的存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陳進國研究員的發言題為《救劫母題:近現代的濟度宗教運動及其動力》,在工作坊學者看來,正好表明香火祭拜式的民間信仰可以通過社、會、壇、堂,轉化為強組織宗教,甚而崛起為劇烈的社會運動,因而產生暴力性的行為。然而,傳統形態的中國宗教(包括儒、道、佛、民間宗教)一般都以弱組織方式活動,相對溫和,并不激進。作為民間自發而弱組織的香火祭祀的廟會、社會,在日常生活中起到了文化傳承、道德維系和社會修復的作用。在這方面,復旦大學哲學學院郁喆雋副教授提交的發言尤其具有啟發意義。郁教授曾以德國萊比錫大學博士論文討論了上海城隍廟廟會在現代城市化過程中呈現的市民社會意義,這次工作坊他以《江南廟會的現代化轉型:以上海金澤香汛和三林圣堂出巡為例》,說明了上海地區現代香火祭祀的復興與傳承。直至二十世紀前期,上海近代大都市建設并未消滅市中心的城隍廟香火,其承續狀態表明它是在市民社會中的“轉型”,而非“消亡”。同理,目前上海周邊鄉鎮的廟會也可以轉型的方式來傳承。但是,不恰當做法,包括過度的商業開發,異化的權力滲透和大拆大建的“建設性破壞”,都會影響其內在進程,產生不良后果。學者們對此現象不無擔憂,而愿意在學術討論之余,以此建言于各界,或能得到更多的關注。
上一篇:復旦朱峰獲評2020上海高校輔導員年度人物 上榜的還有他們
下一篇:沒有更多了